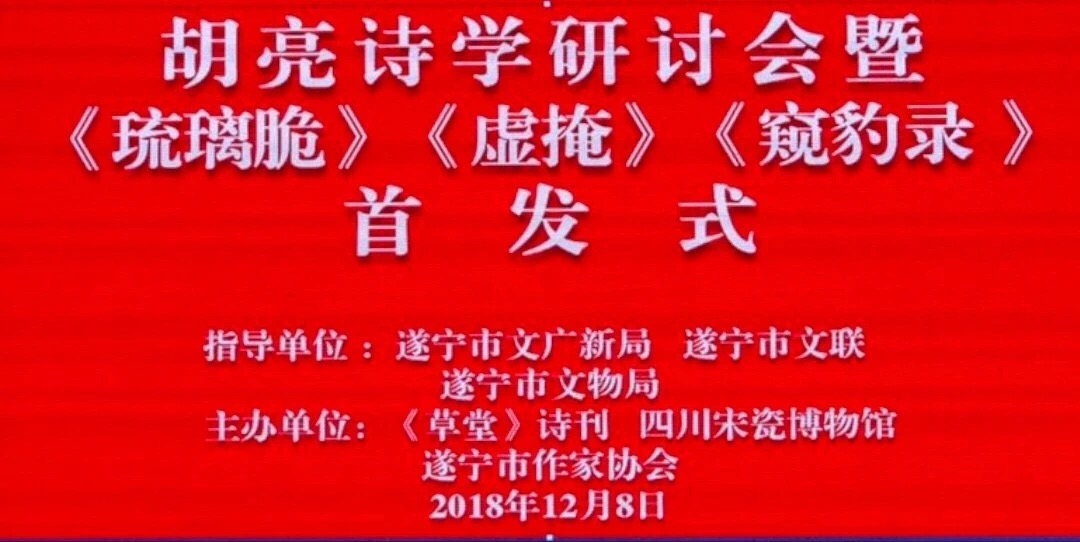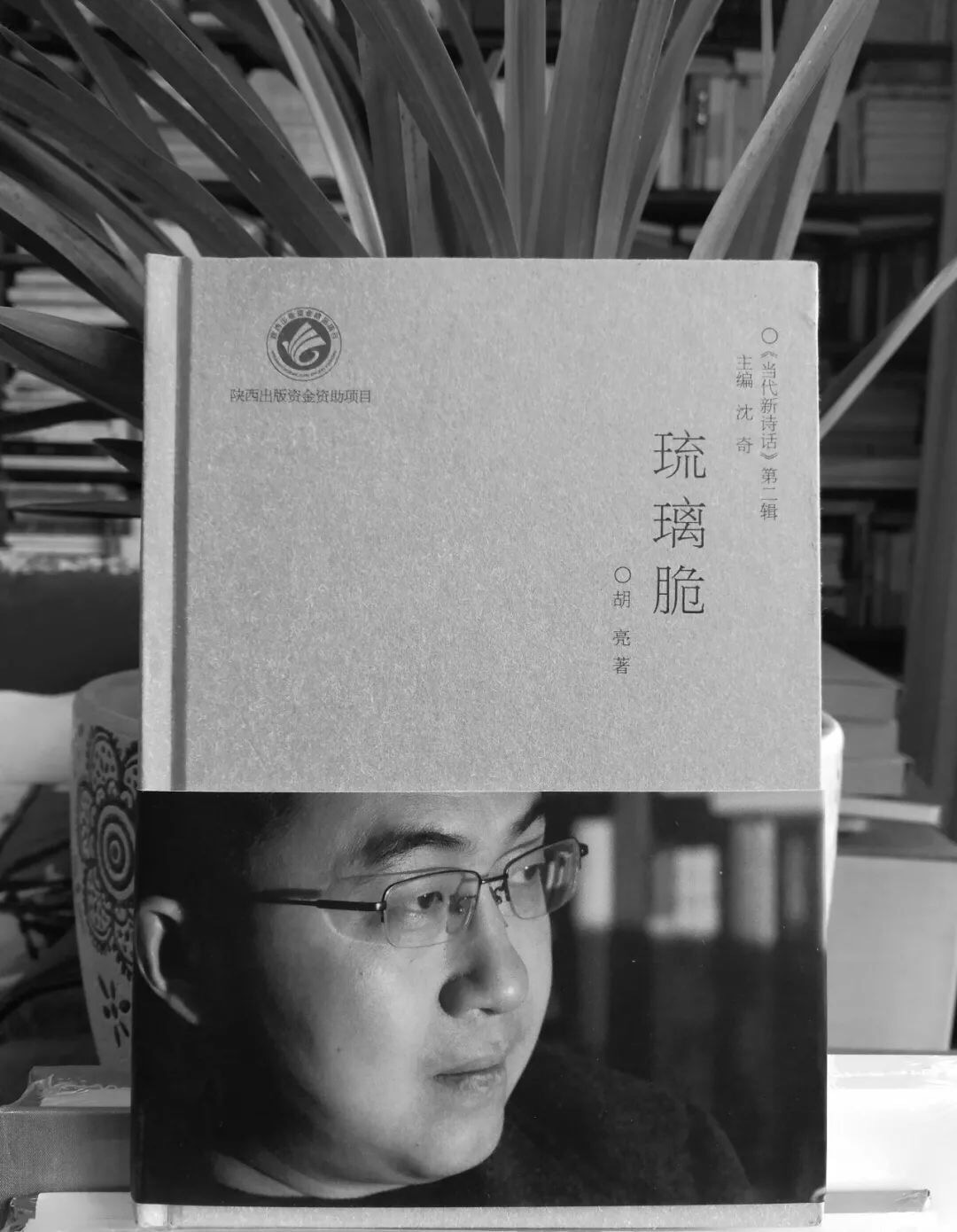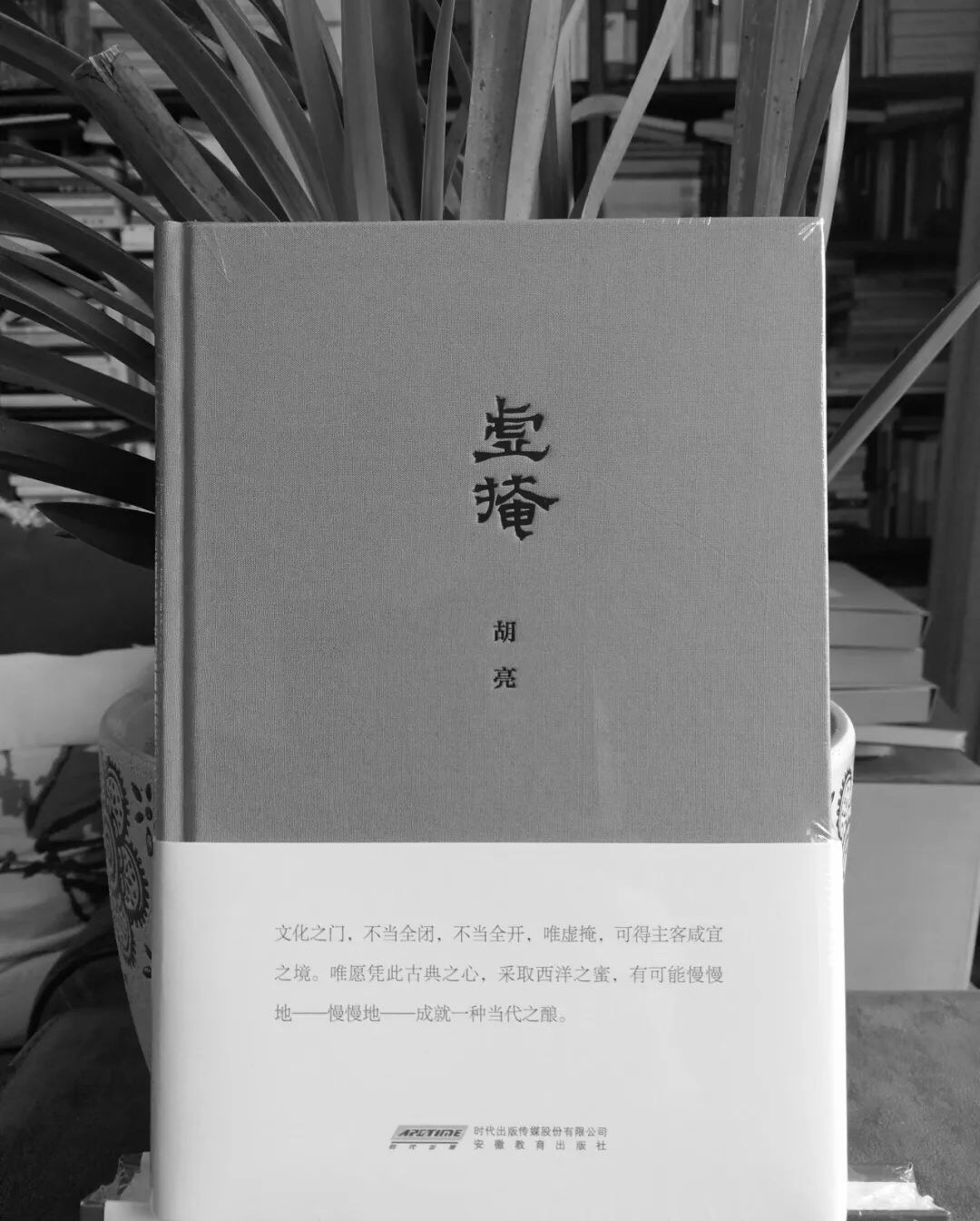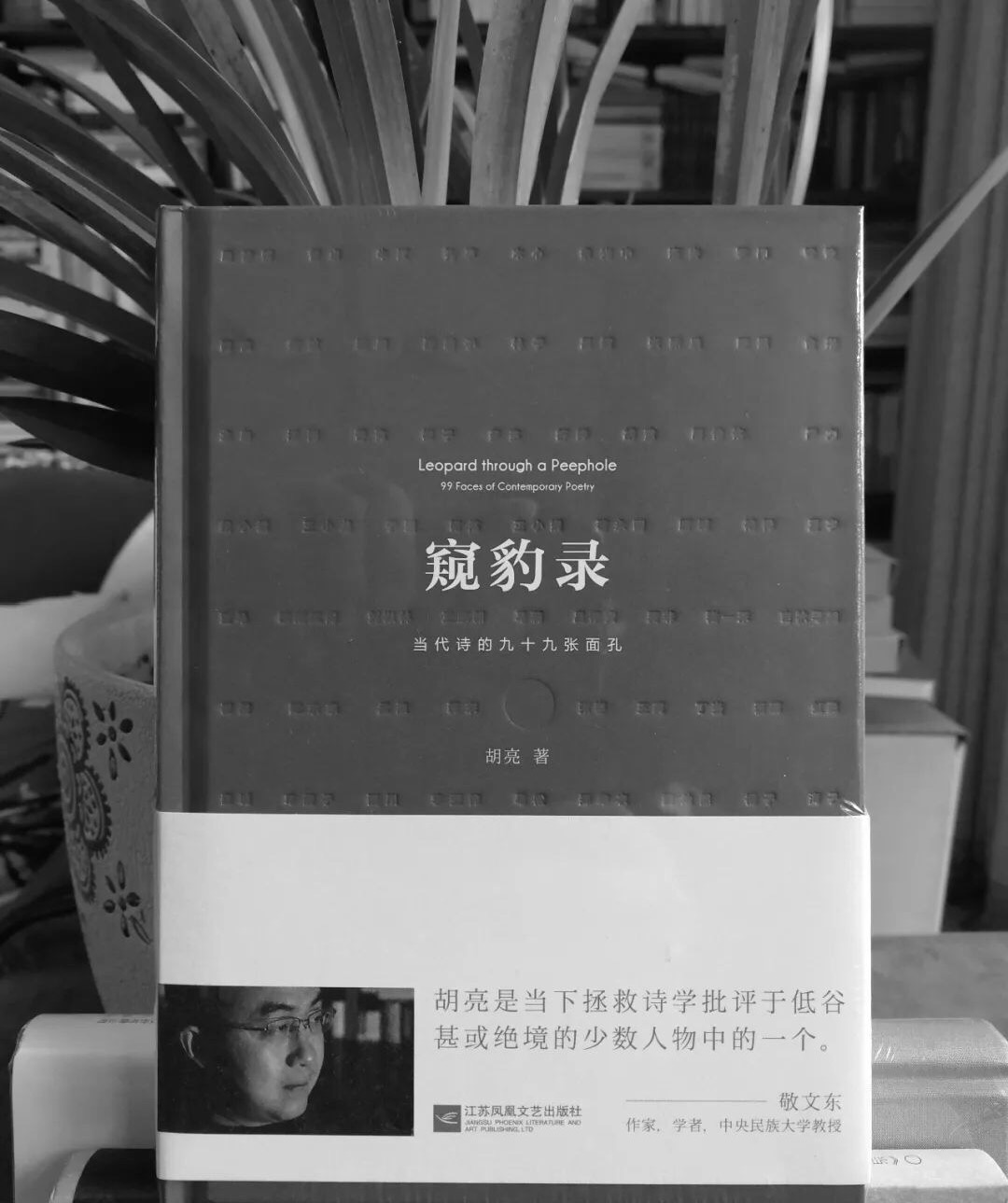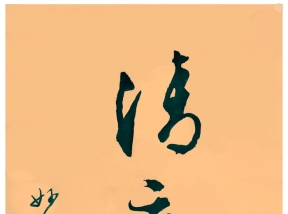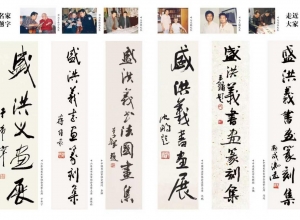查看: 1889806 | 回复: 0
|
主题:1285 | 回复:3178
每日好诗
|
每日诗讯
诗人榜
关注中诗在线

- 微信扫一扫,关注中诗在线

[律诗]
【原】《甲辰秋•关山月》[国际诗歌]
英 诗《 Stray Birds(9. 140)》汉 译《[国际诗歌]
尤里·塔尔韦特诗选(七) Selected[国际诗歌]
英 诗《 Stray Birds(52,302)》汉 译《[国际诗歌]
尤里教授诗选(7)[国际诗歌]
风的眼泪
[诗人]
無花果上曬背的蝶[诗人]
暗夜,用夢吞噬時間[诗人]
原创/现代诗:诗人 作者:孙佳彧[诗人]
诗人[诗人]
诗人创业路[诗人]
女诗人纪念世界读书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