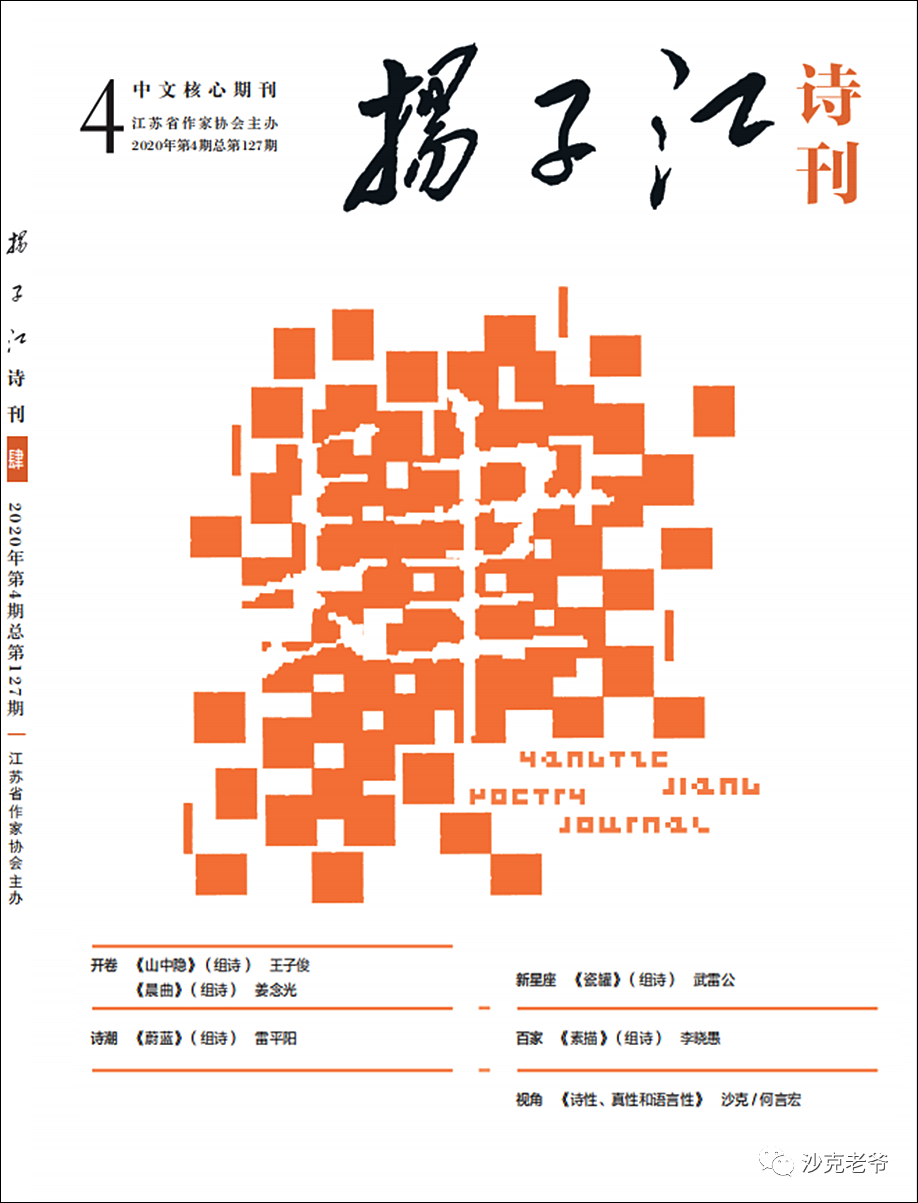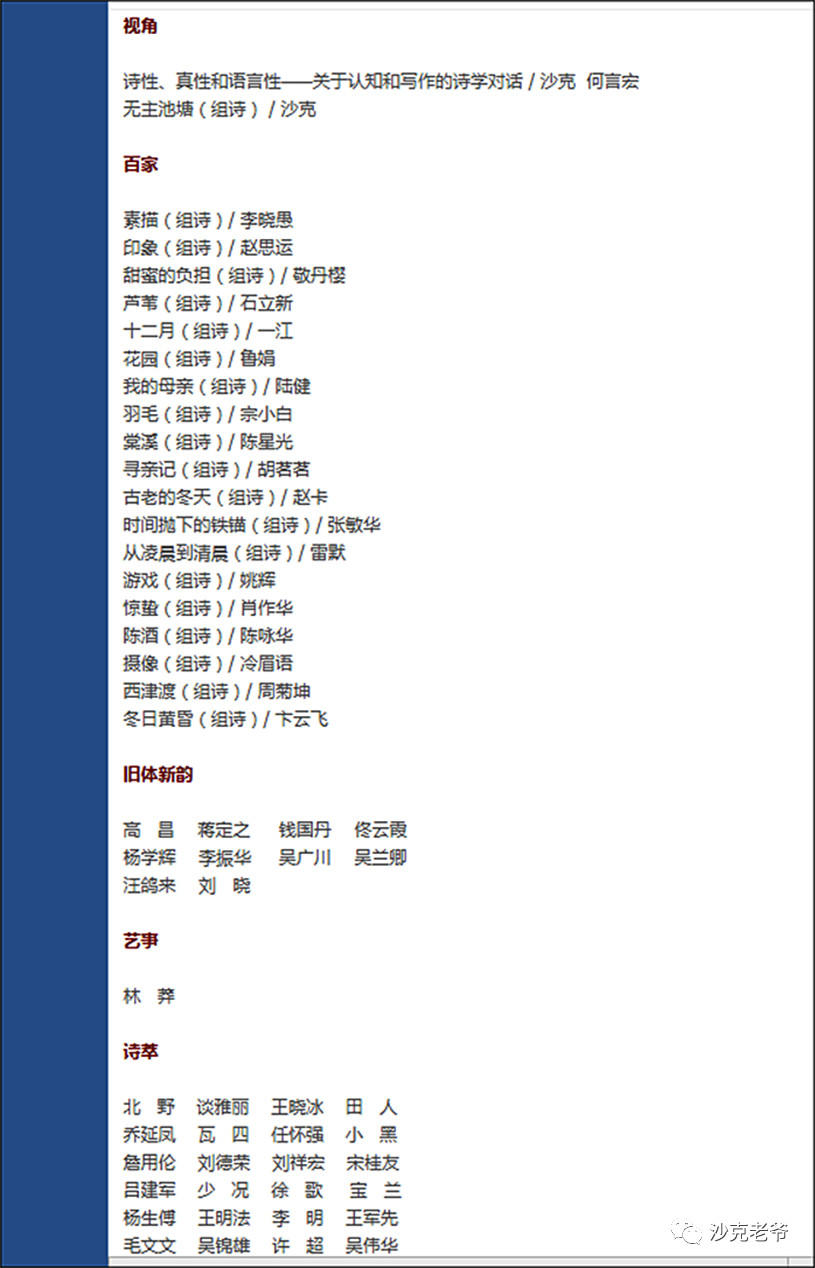本帖最后由 诗坛快递 于 2020-7-14 08:37 编辑
转自2020年第4期《扬子江诗刊》
下图:2020年7月初上海,何言宏与沙克小叙
【诗性、真性和语言性】 ——关于认知和写作的诗学对话 沙克 / 何言宏
一个深怀创造禀赋的诗人,会选择自觉的修辞路径,或者任性地立意行走,虽有弯曲而永不跟风趋同,期求形成诗性的自己、真性的存在和语言性的艺术。诗人沙克对谈文学评论家何言宏,讲述自己自觉又任性的四十年诗路,为异质往于诗坛的文本和人本作深度阐述。
诗性:生命和事物间的深度交感及具体性状
沙克(简称沙):由于诗的不可说和诗无达诂的两极之间存在着无限空域,拿现代诗来对话,需要有个前提和限定,以便深入话题,洞彻内质,说清楚诗理。 何言宏(简称何): 那就开宗明义。你是一位资深的诗人,我们可以就人谈诗,也可以就文本谈诗,从诗学范畴来谈谈现代诗的认知和写作。首先请你回顾一下,有哪几个核心词能代表你的写作理念,在你的文本构成中起着主导作用,促成你的诗学诉求和价值形态。 沙:诗性、真性和语言性,是我诗歌写作的三个核心词,能够概括我的诗学诉求。一个诗人及其写作有了诗性和真性,就有了存在的必要条件;经久地保持诗性和真性,自然地发挥语言性,便会产生某些气质,构成由表及里、由内容到形式的文本价值形态。 在我的诗歌写作过程中,从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,经历了从情绪(主情和抒情)到思想(模仿和思考),从逆反(解构)到调顺(结构)的初级阶段;1990年代度过了从整体(宏大命运)到个体 (艺术和美学),从诗性到真性(精神和存在)的中级阶段,逐步实现自悟自觉。这些履历并非我的主体生活,而是一种诗意生活的隐性过程,也是对词语系统的放敛碰撞的试探过程,无数次的试探后,接近人与物的内生内变的语言性。我从1997年秋天搁置诗笔十年进入21世纪,在2007年秋天重新写诗,仿佛有光阴之灵附体,引领我归位于诗的语言性——词为我在,语言即我,处于生为我思的自在状态。我运行在以诗性与真性为光的隧道中,提炼俗常的物、人与词,构造我写我诗的文本样式;换而言之,这就是我的诗学诉求和价值形态:我的诗与所有人不同,里面有我的诗性、真性和语言性。 何: 你一下子说了几十年的写作历程,表述的意思比较密集,需要慢慢地分解。你能不能扣紧三个核心词,分别解释诗性、真性和语言性的内涵和外延,最好与别人的或者你的诗歌结合起来解释,那样更容易理解,也便于说明你的历练轨迹和风格特征。 沙:断续写作四十年,全无坦途捷径可走,始终是自修自练,弯曲而行,积累了一些认知和经验,以及弯曲中的教训。我来试试看,怎么解释和分享写作中的诗性、真性和语言性,我所说的恐怕百度搜索不到,配套不了某些学说,但不会脱离诗学的应有之义。 何:没有必要去背定义,生搬硬套别人的理论。希望你说出自己的定义、想法和做法,言别人所未言,做别人所未做。先谈谈诗性,尽量谈得透彻一些。 沙:诗性,是诗之所以为诗的本质的和一般的界定。诗性的本质界定,是指它内在于事物、外化为形态的感知属性。可以解释为,没有诗性的文本不能成为诗,诗性比深刻的文学性更为狭义,有诗性的文本未必就是诗。诗性比可感的艺术性更为精粹,富于生动细节的形态可能是艺术,也未必是诗。诗性是人、生命体、自然物的一种或显或隐的传感存在,包含着精神、情绪、形态、状况和态度、行为的综合性。它的外化形态丰富多样,命运抗争、生死存亡、喜怒悲哀,鹰的翱翔俯冲、树的沧桑屈曲、草尖露珠的闪现,奇险的风景、闲淡的市井、恬美的乡俗,恐惧的天灾人祸、壮阔的历史气象、浩瀚的宇宙时空,以及细微的内心活动、入定的苦思冥想等等,万事万物自含生态且独具性状,隐现着可感可悟的诗性。 诗性的一般界定,是指生命和事物之间的深度交感及具体性状。它通过特定的语言结构和组织形式达成某种形态,在某个角度、某个层面或某个维度,表现并胜于那些生命及事物的客观存在,具有主观性很强的审美内涵。只有这样的认知,才能写成诗,否则写出来的至少不是成品诗、好诗。如果在语言构成中削弱、毁坏了那些生命及事物的原有性状,那就不是对诗的造就而是造孽。 何:从你的这些观点,我想到了鲁迅,他那种匕首似的杂文具有深刻的思考,具有典型的文学性,也具有诗性的意味,可不具有诗的一般形态特征,那只能是杂文而不是诗。我还想到,写诗,要在把持诗性的基础上,运用现代诗学和美学里的形式艺术及技巧手法,提炼语言,打磨成一种体式,才能毕竟其功。或者说,没有诗性基础上的艺术形式的构筑,那将是无效的诗歌写作。 沙:完全是如你所说。鲁迅是诗性很强的人,却不能把他含有诗性的杂文和小说当成是诗;体裁和文体的界限必须清晰,否则什么都成了似是而非,怎么认知和写作诗歌。然而,体裁和文体的界限又是相对的,有着特殊性的例外,那要在诗性的基础上品察文本的结构意蕴和外延力如何。例如元代人马致远诗性的散曲小令《天净沙·秋思》,语言技巧和结构意蕴切合诗学性质,完全可以看成是一首诗;近代人尼采某些诗性的哲学箴言,也可以当成诗来读,因为他把“不能存在的”哲学从天上拉回到地上变成“存在的”哲学,涵盖了诗所终极拷问的生命本质。诗性有强弱之分,近代欧洲的法语诗人波特莱尔、马拉美和魏尔伦、兰波,创造了现代艺术的象征主义,虽然它与中国古代诗歌的起兴和传统绘画艺术中的寓兴有所相通,但象征主义高于一般的表现手段和技法,是强烈诗性的通适呈现,渗透进人类进步的哲学思想和文化生活,是从自然与生命内化出来的人文精神。 何:对诗歌这一体裁来讲,不同诗人的写作也有文体的不同,从而呈现出诗性的彼此差异。就说西方的象征主义,它好比是诗歌的一种文体,与古典主义、浪漫主义、现实主义的文体显然不同,前后者所呈现的诗性区别很大。回到我们的当下,从文本认知的角度,你怎样理解诗歌体裁中的文体构建。 沙:在诗歌体裁之内作出文体区分,是对诗和诗性的高级识别。拿现代诗人李金发与戴望舒来作比较,其文体差别非常显著,前者的象征主义是对诗性的浓缩异构,后者的象征主义则有对诗性的唯美演绎的倾向。有时候,诗性还可以让诗与其他艺术隔类同体,例如中国古代诗词的起兴手法是常识,而所谓“诗画一体”,连结之处正是传统绘画的寓兴。寓兴类似于古代诗词写作的起兴,是随境联想他物,随心起兴此体,创造出动态事物的意象或超象,这就是诗性与画性的隔类同体的动因。 何:所谓诗性,正是古今中外诗歌传统的根本,就像人性是人之为人的根本。诗性的内在蕴含是血质气性,而起兴是一种具体的写作方法,光有诗性而不能起兴,也写不好诗。 沙:在中国古典诗人中,李商隐、韦庄、温庭筠都是善于起兴的宗师,自唐以降的古典文人画的性灵、神韵和逸品之说,都是在追求超脱身心的诗性境界;到了明末清初的四僧画家那里,常常以寓兴手法作画,寓此体而兴他,也是一种诗性表达;虽然他们也会题诗,其艺术方式与象征主义相比,在适用范围、程度和系统性方面,还属于文人画家的个性思想和个别技艺,并不能普适于世风规范;而象征主义则相当于“通用的科技”,在文化生活中无处不在。在现代欧洲的德语诗人里尔克和保罗·策兰包括女诗人拉斯克·许勒的身上,集中了“诗性的铀”,他们历经民族、家庭、肉体和心灵的暗黑命运,有着对外部世界的超敏反应,且洞悉内在生命的美好和异化,竭力呈现人生处境的内核状态;他们是现代主义反叛精神与后现代主义解构精神的结合体,这种20世纪的人性精神,就是他们最大的诗性。 何:自古以来,无论亚里士多德的《诗学》、贺拉斯的《诗艺》,还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诗学思想,都是东西方诗文化的传统经验和理论精髓。近现代以来的世界诗歌,在形式构成、内容含义和价值诉求上,最终在文体和诗性上,都与古代诗歌大不相同,那就是工业文明生活的现代性与农业文明生活的自在性的不同。我们还是回到汉语现代诗,请你列举两首诗为例证,最好是你本人的诗,来说明诗性写作的得失。 沙:用自己的诗例来说优道劣,等于拿手臂去抵挡一把双刃剑,反正会伤及自己。早年我在寻求诗性方面比较努力,比如有一首《冬夜的行走》(1983年),它的指代、寓意和象征的活跃形态,或许包含了一首诗所必备的诗性,或许也具有诗学的形式特征,它的内容则留有多向的解读通道。再比如《阴谋和爱情》(1985年),以思辨性来显示一些诗性,然而它对莎士比亚经典悲剧的复述、铺陈和说理,流于物理层面,情绪太过,损伤了一首诗所必须的含蓄、精炼和弹性。两首诗相比较,前者在诗性之上具有现代美学性,后者诗性不足且欠缺太多,如果作价值判断显然是前优后劣。
真性:人本状态——归于自然、物理和本能
何:下面我们可以转换话题,谈一谈诗的真性。诗的真性,是真善美、假丑恶的那种真,还是广泛的现实主义?我有一个观点,文学包括诗对现实生活应该负有介入功能,可能属于或者说应该属于诗的真性范畴。 沙:诗的真性比较简单,它是所涉事物的原有属性。它不是俗常伦理的“真善美、假丑恶”的人为判断,这种判断含有意识形态的、道德的、文化本位的倾向性,对诗来说可能属于局限自利的强词夺理。诗的真性是人本状态,归于自然、物理和本能之中,没有娇饰和伪装,即使有认识论上的倾向性,也是进入高级层面的哲学思量。比如,爱这个词,有无数的解释,维护生命的意愿、行为和状态都是爱,而不仅仅是人和动物的爱情或情感,爱有时候是生命之为生命的生理本性,也可以是相关的自然物的呈现,比如江海山川、树木花草、风景气候的适宜性,便含有那种温情。这些爱都是本真的,写在诗中就是真性的成分;如果把自然的月色海景附加上地域、体制和族群的人为界定,什么“西方的月亮比东方的圆”,或者“东方的大海比西方的美”,就削弱遮蔽了月亮和海的真性。. 何:在我的理解中,荷尔德林诉求的原乡,属于诗中的真性,相对于通常的居地、家乡、故乡,它是真性的存在,不带情绪色彩和附加物,仅只是灵魂的栖所。说到这里,还是要就文本谈诗,请你对照自身写作,再举一首例诗说明这种真性。 沙:在重回诗歌写作的最初几年里,我重视对文本真性的自审,不能通过自审的就舍弃掉。我写过一首《被抬举的羔羊》(2012年):“站着的那人把羔羊举过头顶/身后一群人跪下/对飘移的浮云倾诉愿景//草地颠倒,圈棚飞旋/羔羊晕啊,颤抖,哭喊,挣扎/不愿意自己高过大家//它不识抬举,识得明晃晃的快刀/插在那人的腰间/为捧得老高的它准备//为虚幻不定的浮云准备/一把快刀,用羔羊的纯净和恐惧/涤荡一群人沥血的心//不用试探。看着羔羊的命运/跪着的人群觉得被抬举//似乎与站着的那人一样的高”。或许它呈现了原乡式的真性——人性和动物性,不掺入情绪、道德和结论等附加物。 诗的真性与事物的本质性相近而又不同,它必须切入和掘现事物的内质,还要凝练出事物的形态征象,去反映人与物的规律性关系,凸显生命性的情状。一只献祭的羔羊,被祭祀者抬举着高于众人,它挣扎着不愿做牺牲品,而跪拜的众人习以为常毫不怜悯羔羊的处境,也不觉得自身命运被捆缚,相反认为自身的精神与祭祀者一样高扬。这样的诗意叙事,是想抓住人类生活中的本真状态,体现深藏的哲学意味——祭祀者腰间的快刀,容不得虚假,在那里闪亮着无是无非的光泽。 何:既然真性是对事物本性的呈现和表达,必然受到人生经验的影响,我认为《被抬举的羔羊》对现实生活有着很深的介入性,含有文化反思和人性批评的成分。 沙:怎么阅读解释一首诗,主要是读者的事。我写作《被抬举的羔羊》,尽量隐忍介入现实和反思批评的意图,以保持单纯的真性。当然,你的阅读解释正是一种引申的真性。
语言性:语法修辞功能与个性特征的结合
何:继续进行我们的话题。你对诗的语言性的想法是什么,那是语法修辞的功能还是个性的语言特征,或者是两者的结合。另外请你说说,怎样把诗性和真性融入到语言性中。 沙:诗的语言性是比较复杂最为关键的问题,简而言之,它是语法修辞功能与个性特征的结合。语言性划分了体裁和文体,也区别了同类体裁和文体的层级。一个没有语言性的人,非但做不了诗人或其他体裁的作家,也做不好非文学类的写作者。这里的语言性,指的是对于语言本质及其使用规律和变化可能的认知,对于语言的艺术性和美学性的把握,它是诗歌创造的才能和品质。有了语言性,才能写作诗歌,要不然,就是运用语法修辞对现成语言作排列组合和技术复制。诗人海子创造过一个关于想象力的简单判断句,“海鸥是上帝的游泳裤”,它体现了比较强烈的诗性和语言性,妙在主宾语之间发明性的远距离组合;假如改成“海洋是上帝的游泳池”,尽管也是诗性的隐喻表述,由于喻体和本体关联空间太近,换汤(喻体的游泳裤变成游泳池)而不换药(本体的海鸥变成海洋——还是属于水域的存在),其语言性就弱多了,等于人们常说的某某湖泊、水塘是王母娘娘的洗浴池,作为传说显得很神奇,作为写诗的想象力就太逊色了。 何:诗的语言性规范在哪里?以现代诗人李金发与穆旦为例,我认为他们的文本都是现代性比较强的,基本是象征主义的路子。他们在语言性上的区别,是现代诗的产生时期、诗学理念和构成方式的多种不同。 沙:李金发与穆旦的语言性差异的原因,已经被你点明要点。文学语言特别是诗歌语言,远不是既定的语法修辞所能涵盖限制的,否则文学语言就无从产生,语法修辞就不会进步。反过来讲,诗的语言性对于常规话语规律的服从,一般是指写诗不能作无理性、无创造的随意拆拼。从孔子、屈原到枚乘,唐宋诗人到曹雪芹,包括“五四”诗人及鲁迅老舍都发明过词汇、语言和修辞法,随后被纳入现代汉语词典;为什么“现场”的诗人就不能创造词汇和语言了,仅仅写几首好诗进入某种阶段性史,就是优异杰出的诗人了吗,完全不是。越过当代而留存下去的诗歌,肯定不是趋附于时势定律的那些内容,肯定是语言性显烈、富含诗性和真性的那些文本。李金发的语言性是典型的象征主义,例如他的诗《弃妇》和《迟我行道》,含有黯淡的直觉,新异的词语组合,浓郁的隐喻,可其现代汉语的进化还不够彻底;穆旦的语言性已从象征主义向现代主义过渡,调用了成熟的现代汉语,既有完整性又有分化性,例如《城市的舞》和《森林之魅》,与二战后的西方诗歌精神比较接近。 何:我在想,语言性的因素和作用,在现代诗的认知和写作中主要体现在那些方面;语言性对诗歌品质有多大的影响,它是一套理论说词而已,还是与写作密切相关。我们时常看到说的是一套,写的又是一套的现象,造成理论的脱轨架空,写作的自生自灭。 沙:语言性主要体现为能,即各种能量,它包含语词、语序、语韵、语速、语态和语性、语质、语义等等元素,以及各种形式因素和技法手段造成的微妙语感,最终凝结为语言的所指和能指,释放出能量,左右着语言结构及其符号系统。 我在1980年代中期就有了切身体会,语言是有能量的,主要包含物理性的势能、动能,它偏向于思想和才华;化学性的反应能,它偏向于性质、时机或动机;生物性的智能、热能、本能、技能等等,它偏向于性情和存在性。以当代诗人的语言能量来作比方,北岛、杨炼以势能见长,优于语言的重量、高度和力;顾城、车前子以动能见长,优于语言的质量和活跃性;舒婷以热能见长,优于语言的情绪和心理;梁小斌以智能见长,优于智慧和深度;继续往下作比方,海子是本能杨黎是技能,于坚和默默是反应能……溯源到中国古代,屈原是势能、动能和智能的合成,李白是动能、本能和热能的合成,杜甫是势能、反应能和智能的合成,李商隐杜牧是智能和技能的合成,苏轼是势能、动能、反应能和智能、本能的综合。 何:你这番说理,是基于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的语言符号学理论,被你化用得很有些新鲜感,似乎也有些道理,可是缺少论证依据,姑且聊备一格。我肯定认为语言是有能量、有力度的,可是把物理、化学、生物的能量引用到诗的语言性中,显得有些勉强和玄虚…… 沙:我坚持这个观点。能量,是语言性的重要指标,就像活力是生命性的重要指标;能量是分种类的,能量值与语言性的丰富复杂程度有关,没有一个中外大诗人不具有复合的语言性。语言性单薄的诗人,常是类型诗人或技工诗人,举目望去比比皆是。 何:我要反问一下,没有所谓的语言性,就不能写出好诗吗,也许我可以换一种认知角度,有思有技巧才能写出好诗。 沙:没有语言性一定写不出好诗,语言性不仅包含了技巧,决定诗的风格特征,而且能生动形象地体现思。思对文学很重要,对诗极重要,那必须在语言性的发挥中获得效果,形成语言能指下的多解。把带点哲理思考有点技巧手法的文本,当成诗的一种高标,是长期以来对诗的狭解误解。比如说“狭路相逢,勇者胜;万里跋涉,恒者至……”,用类似的思路铺排语言,根本就不是诗,只是一般修辞下的哲理常识。 没有语言性的所谓诗人,首先对诗歌语言缺乏感知意识,其次弄不清诗歌语言和其他语言的性质区别,最后总想借助其他语言来填充文本躯壳,这样岂能写出好诗。不论他们有多大的声誉气场,还是相当于那些没有色彩造型感的劣质画手,无论他们多么当红吃香,却肯定不是合格诗人。借用一句俏皮话,或许能说明某些集体无意识的界限混乱,一个不会理发的医生不是一个好歌手。
对应:理论观点与自身写作进程的关联
何:我们交谈到现在,可以作一个小结。诗性、真性和语言性是诗歌的内在属性,在具体写作时需要运用题材、角度、构思、技法等等,构成形于外诚于中的文本。回到你自己,怎么把诗性、真性和语言性运用到写作实践中。 沙:写诗有年的人,都有个学习、练笔,磨砺、成熟,反省、跃升的过程,有时是时间维度的,有时是空间维度的,有时是脱胎换骨后的否定之否定,然后才有可能处于诗性、真性和语言性的融通状态。 何:自我反省,否定之否定,是写作的源动力。你能否列举一些节点性的诗歌篇目,来说明自己的写作状态和进程,这是理论联系实践的关键,或许也是对话的意义所在。 沙:前几年我和严力、默默两位诗人谈到过我早期的诗歌写作,那是我1980年代的诗生活,“我怀揣神秘和野蛮,左冲右突往前走、往后退,实现必须的存在感。我想起千手佛,朝各个方向伸手,却不去抓住什么。到了1988年,我形成了价值、语言、手段的自我风向,才把此前此后的写作连成一根主脉络,贯穿至今,那就是从自发到自觉、再到自在的真实内容:意象与心象,隐喻与自白的合一。” 那十年中的节点性诗歌有《冬夜的行走》《电线上的燕子》《蹲在猫背上的启明星》《不同的九月》《命运》《战争与和平》《远方之远》等等,它们从启蒙走向理性,从现实走向思考,从生活走向信仰。总的来说,此期的写作虽然也有《不同的九月》那样语言性强烈的诗,《电线上的燕子》那样倾向真性的诗,主要还是期求诗性的多元表达,像《冬夜的行走》《蹲在猫背上的启明星》那样的隐秘情绪,像《命运》《战争与和平》那样的困惑和思索,像《远方之远》那样的极目远眺,都是诗性至上的,尽管彼此间常有观念冲突,却都在趋向“意象与心象,隐喻与自白的合一”。 何:接着说,你在1990年代、新世纪以来的诗歌写作中,呈现什么的变化,或者讲有那些进步。 沙:1990年代我的诗歌写作逐步进入所谓的自觉期,特别注重真性,包容量变大,与社会处境和自身处境两头贴近,让自然、生命与生活同在;此外,在关联思考的基础上退向情绪和抒情,这是迂回规律中的退后和写作方式的变化,为的是深入真性的空间,却没有时间上的进步。比如《摩特芳丹的回忆》《受伤的鸟》《大器》(长诗)《回故乡之路》《大地清唱》《风啊往一个方向吹》《黄金时代》《本身的光》《一粒沙》等等诗歌,都是真性的生存体验和自我命运的书写,并存着明显的诗性和相对的语言性,大体还是以书写真性的“我”为主。 我离开诗歌的那十年,转身致力于新闻职业和生活本身,偶尔写点诗也是放在抽屉或电脑里。2007年回归写诗后,进入了自在的诗生活。写什么怎么写,写多少,都是自在而为,不考虑适不适合发表。事实上,近十多年来我的诗歌写作比较频繁,也有不想写时的短暂休止,写作总量不比上世纪少。至于我回归后的诗学认知,完全不同于早期和中期,我把语言性放到首位,把诗与作用、目的脱钩…… 何:我对你回归写诗以来的作品比较关注,比如2000年代的《消灭语法与修辞》《春天致我》《和谐的园子》《有样东西飞得最高》《无主的池塘》《辽阔》《弄醒一块沉睡的金币》和长诗《死蝶》等等;2010年代的《单个的水》《向里面飞》《一只不想的鸟》《别对我说大海》《忆博斯普鲁斯海峡》《思卢沟桥》《低温抒情曲》《动摇》和长诗《民》等等,我觉得其中的思和技巧占上风,深邃而纯熟,也感觉到了语言性的无处不在。 沙:语言性的功能,与写作能力对等存在。在你提到的这些作品中,我把语言当成自有生命的伙伴,与我互感互动构成文本的形式和内容,而不当成是表达什么、获得什么的使用工具。语言性的功能实质是,语言本身自带诗意,写作者邂逅和选择它们,彼此感应促动而产生文本。 何:我想插入一个相关的话题,与对话的主题是吻合的。在儒教文明的传统中,仁义礼智信是其内核,克己节欲是做人的高标,似乎把情与爱关在笼子里了。其实仁是宽泛的,含有生命的情绪和爱,积极表达爱则含情脉脉,消极表达悲可嚎啕欲绝。在现代诗写作中,主情者比主智者多得多,抒情性始终昂然成风。 沙:抒情性是诗性中的一种因素,诗性最初对应抒情性,然后是日常性,当下是智性。真性对应的是客观事物及自我存在的互感,语言性对应的是风格特征及其文化容量。在我们这个溢情太多,迟于西方进入现代、后现代,渐渐与世界同步的数字化时代,早已远离了两百年前的西方浪漫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的社会,那种抒情写作方式过期太久,真地该醒一醒了,今天还沉迷其中太不明智,那是在做虚假的穿越游戏。写什么都啊啊啊地高温抒情,连超市货单和餐厅菜单都可以朗诵得激情洋溢,能有多少的诗性真性。也许国内诗歌界不太了解,世界各地很难看到这样的抒情写作和诗歌朗诵,人家写的读的,正是当下生活方式中的现代诗,写作追求智性,朗读淡化表演。高温至极必然熔断,两百年前的长辫子和裹脚布早已不是“忠实情感”的性状,今天还守持它们就是矫情作假。诗歌必须进步,抒情退后,智性靠前,至少让热抒情降为低温抒情,也要让过冷的理性虚蹈升级为语言性的思想叙事。 何:我觉得你的诗学思考比较多维,却又把纯粹性看得很重,而且在“与时俱进”,然而多维思考必然带来丰富性和复杂性,对纯粹性产生夹击。 沙:在诗学认知上,我拒绝“与时俱进”这样的机会性理念,遵循空间维度的写作规律。诗人的纯粹性,未必指一辈子用相似手法写相似格调的诗,比如戴望舒;未必指一辈子写及物言虚或灵魂虚蹈的诗,比如顾城;未必指一辈子写及物喻物、抽象思想、所指现实的诗,比如臧克家;未必指一辈子写冷抒情、日常口语的诗,比如韩东。诗人的纯粹性在于清晰的诗学、美学的指向性,价值观的坚定性;纯粹性向来不是伟大诗人的重要指标,相反在上述指向性和坚定性的范畴,有多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才有多大的诗歌造化,歌德、波德莱尔、里尔克、洛尔迦、艾略特,还有索尔仁尼琴、米沃什莫不如此。 何:如果在纯粹性和丰富复杂性之间作选择,你倾向于哪一方。 沙:你为什么抓住纯粹性和丰富复杂性的问题不放,是不是怀疑我的写作纯粹性不足,丰富复杂性有余,影响了诗歌文本的价值实现。 何:不是抓住不放,是要把问题说清楚。我觉得诗的纯粹性特别重要,比丰富复杂性更能凸显价值所在,有时候“丰富复杂性”是一种托词,当一个诗人的思想坐标紊乱,过分随意地写作,会疏远和损伤诗的纯粹精神,这时就会用“丰富复杂性”来自我辩护。 沙:好,你说的很痛彻。然而,人们所指称的纯粹诗人,往往代指他写作格式的一致性。我早在写于1992的诗论《关于现代诗的泛思考》中说过,“风格是作家诚于中形于外的精神个性在作品中的体现,是其作品在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中所表现出来的独特性。……刻意地用同一种形式和主题性的内容制造风格,给重复自己、匠工制作提供了理由和便利。”现在我不但坚持此论,还认定这种重复自己、匠工制作的“理由和便利”,是没有禀赋和创造力的衰象。我所理解的纯粹性,不是形式上的类型化、技巧上的模式化,尽管这样写作可以讨巧走捷径;我认为纯粹性是指精神理念的恒定性,文化立场的明确性,语言艺术的探索性。丰富复杂性,指的是生命状态和表现内容的多样性,手段手法的变化性,它们体现在我体量较大的组诗或长诗中,或者是足够样本的短诗中。
尾声:关于文化源流和诗歌谱系……
何:文化源流,诗歌谱系,对成就一个诗人非常重要。在我的印象中,你是一位靠才气与思考写作的诗人,才气可以标新立异,思考可以自成一体。 沙:现代诗写作,仅靠才气和思考可能走不远。相反,谁有再大的学问再多的知识和人生经验,都可以用来写诗,关键是怎么用,是否合乎诗学和美学而用得恰到好处,用得不恰当会适得其反,挤兑迫害诗意。汉语现代诗的历史只有一百年出头,它从西方的诗文化中横植过来,一直存在着对传统文化水土的适应问题。看起来现代诗没有定规,谁都可以写,其实它类似于西方的大学,入门容易毕业难,而传统诗词类似于中国的大学,可能是入门难毕业容易。唯有融通东西方的诗文化,才能创建精致的形式和精粹的内容,否则就会有穿马褂打领带、穿西装戴瓜皮帽的夹生感。那种无分中西款式的休闲服,便像是现代诗的一种普适装束,里面的身子骨泾渭分明,谁帅谁有气质,那得看内外在素质。 何:对诗性、真性和语言性有了觉悟的诗人,无论承接了什么文化源流或诗歌谱系,只能作为潜在的背景或台阶,而不能作为写作的法规和惯例,那样会变成包袱重压在身,走不出历史与现实,成不了愈行愈远的自我风格。 沙:我深表同意。对接和借助传统文化的源流,踏过某些台阶后便要脱身,独行自立。我们的社会处于数字化的高速高效时期,一夜网红层出不穷,仿制和拷贝易如反掌,要想独立出来比任何时候都难,那需要无比强韧的自撑力,不仅能承接文化源流或诗歌谱系,而且能融入超出诗歌的人类文明和生活方式的进步性,形成自主产权的芯片式的自我存在,里面包含着哲学认知和诗学信仰,对我来说那是四十年不变的指向:生命、自由、艺术(美)和爱。 何:记得十多年前,我为你的文艺理论批评集《心脏结构与文学艺术》写过一篇阅读感受,题目用的就是你这种理念的“生命、自由、艺术与爱”,看来你是终身锁定了这种价值诉求。……我们虽然在前面设定了封闭性的话题,说了半天还是逾越了一些框限,通向开阔的相关性,这样反而增加了交谈的支撑点。一场对话交流,对接了相应的理论与实践,不可能面面俱到,假如是谈透了一些诗学问题,比处处点到为止要好。 沙:言犹未尽,却已窗明心亮。说得好不如写得好,如果我还能持续写诗,必将无休止地切近诗性、真性和语言性,求索诗途终极的更多密码。
(对话于2019年冬) 2020年第4期《扬子江诗刊》部分目录
摄于2008年南京。沙克远离诗坛十年后于2007年回归写诗,不久"遇见"高中老同学何言宏,被他和叶延滨、车前子、胡弦、罗西、义海、冯光辉、祁人、雁西等等一大拨1980年代的老诗友们再次扯上当代诗歌的"贼船"
|